舊的設計.新的海旁

藝術中心原初設計模型,留意通往對面公園的平台和連接演藝學院的橋,最終都沒實現.上週政府公佈灣仔至北角的海旁發展計劃,把藝術中心和演藝學院一帶列為藝術文化區,發展成市集和公開表演場地.我希望,這個設計能實現.
Labels: 藝術中心
在城市裏,自然消失了,我們不會感懼上帝造物的神奇偉大,因爲我們被我們自己製造的符號包圍。城市就是人類文明的表像,把城市擬人化,愛上城市,就是把人類物化,愛上自己。大家試幻想,衆多對城市文化的觀察,所有有關城市生活的文藝創作,都是人和鏡子的對望,一封寫給自己的信。或纏綿抵死,或耐心叮嚀。主題只有一個──我,或者我們

Labels: 藝術中心
 要回答這個問題,首先要知道藝術中心成立的歷史.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後期,香港只有中環大會堂一個現代藝術場地.那時,政治動蕩剛過去,經濟開始蓬勃.藝術活動增多,場地嚴重不足,很多藝術團體都抱怨租不到大會堂的劇院和展覽廳.其中有些人便醞釀向政府申請土地,興建一座藝術中心.這些人都是藝術愛好者,來自不同藝文團體,由白懿禮(S.F. Bailey, 他當時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秘書長)牽頭.他們的構思是,政府只需要提供土地,他們負責向社會各界募捐建築費,興建一所綜合藝術中心.根據他們的構思,這所藝術中心是財政獨立的,並不需要政府資助運作費,主要收入來自辦公室樓層的租金收入,捐款和票房收入.
要回答這個問題,首先要知道藝術中心成立的歷史.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後期,香港只有中環大會堂一個現代藝術場地.那時,政治動蕩剛過去,經濟開始蓬勃.藝術活動增多,場地嚴重不足,很多藝術團體都抱怨租不到大會堂的劇院和展覽廳.其中有些人便醞釀向政府申請土地,興建一座藝術中心.這些人都是藝術愛好者,來自不同藝文團體,由白懿禮(S.F. Bailey, 他當時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秘書長)牽頭.他們的構思是,政府只需要提供土地,他們負責向社會各界募捐建築費,興建一所綜合藝術中心.根據他們的構思,這所藝術中心是財政獨立的,並不需要政府資助運作費,主要收入來自辦公室樓層的租金收入,捐款和票房收入. 就算是今天,這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構思;但在當時,因為有很多藝術團體的支持,而場地又真的不足,經過幾年的游說,政府終於答應把灣仔告士打道外面新填海區的一塊小土地交給他們.這塊地小得不能再小──只有一百呎乘一百呎,能建得甚麼東西出來?這工作交由當時三十幾歲,剛從美國回來的建築師兼藝術家何弢.結果,他不單用盡這塊地可建的面積,設計出一座十六層高的垂直式的藝術中心,裡面有展覽廳,劇院,演奏廳,實驗劇場,課室和圖書館,這建築同是亦是一件前衛藝術品,以三角形為主題,在大樓的不同地方呈現,又把鮮黃色的冷氣喉管外露,成為串聯起不同設施的裝置藝術,這大樓獲得過本地和海外的獎項,到今天已被視為七十年代香港最重要建築之一.
就算是今天,這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構思;但在當時,因為有很多藝術團體的支持,而場地又真的不足,經過幾年的游說,政府終於答應把灣仔告士打道外面新填海區的一塊小土地交給他們.這塊地小得不能再小──只有一百呎乘一百呎,能建得甚麼東西出來?這工作交由當時三十幾歲,剛從美國回來的建築師兼藝術家何弢.結果,他不單用盡這塊地可建的面積,設計出一座十六層高的垂直式的藝術中心,裡面有展覽廳,劇院,演奏廳,實驗劇場,課室和圖書館,這建築同是亦是一件前衛藝術品,以三角形為主題,在大樓的不同地方呈現,又把鮮黃色的冷氣喉管外露,成為串聯起不同設施的裝置藝術,這大樓獲得過本地和海外的獎項,到今天已被視為七十年代香港最重要建築之一. 這是一九七七年.香港人口突破四百五十萬,廉政公署成立,九七仍很遙遠,香港正邁向她歷史上最繁榮富裕的年代.很多年青藝術家從外國念書回來,想把風起雲湧的當代思潮帶回來,懷著對社會和藝術的理想,把香港變成中西文化互相撞擊的實驗場.而藝術中心,這所從開始便是民間主導,從開始便華洋混雜,亦從開始便欠下一大筆債的藝術中心,便成了這個場實驗的出發點.
這是一九七七年.香港人口突破四百五十萬,廉政公署成立,九七仍很遙遠,香港正邁向她歷史上最繁榮富裕的年代.很多年青藝術家從外國念書回來,想把風起雲湧的當代思潮帶回來,懷著對社會和藝術的理想,把香港變成中西文化互相撞擊的實驗場.而藝術中心,這所從開始便是民間主導,從開始便華洋混雜,亦從開始便欠下一大筆債的藝術中心,便成了這個場實驗的出發點.Labels: 藝術中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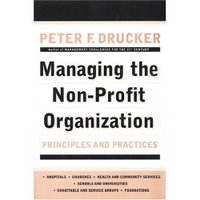 企管大師杜拉克,晚年致力推動「非盈利和非政府機構」(NGO / NPO),1990年,他寫了一本書,叫【管理非盈利機構】(Managing the Non-Profit Organisation)成為這課題的經典作品,書中劈頭第一句便說:「非盈利機構存在的目就是改變個人或社會」.這句話真正擲地有聲,正好對應經濟學家佛利民的另一句名言:「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帶來利潤,並無其他.」佛利民的話說得這麼絕,是為了回應近年社會愈來愈要求企業要負上「社會責任」的風氣,即是說除了要守法外,企業還要發財立品,做好事.
企管大師杜拉克,晚年致力推動「非盈利和非政府機構」(NGO / NPO),1990年,他寫了一本書,叫【管理非盈利機構】(Managing the Non-Profit Organisation)成為這課題的經典作品,書中劈頭第一句便說:「非盈利機構存在的目就是改變個人或社會」.這句話真正擲地有聲,正好對應經濟學家佛利民的另一句名言:「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帶來利潤,並無其他.」佛利民的話說得這麼絕,是為了回應近年社會愈來愈要求企業要負上「社會責任」的風氣,即是說除了要守法外,企業還要發財立品,做好事.
 如果對社會企業有更多興趣,可以讀【如何改變世界──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】,作者是美國的戴維.伯恩斯坦.這本書介紹了世界各地社會企業的例子,和背後推動的社會企業家,亦分析了這些機構和人物為甚麼能成功改變社會.譯者是【窮人的銀行家】的譯者吳士宏.吳士宏的故事也很傳奇,她是中國第一代打工女皇,曾任IBM, 微軟和 TCL 的高層.2003年,她高調離開企業生涯,立志要在中國推動社會企業.看她說做就做,首先就埋頭譯了兩本好書,似乎是來認真的,真的要改變世界.
如果對社會企業有更多興趣,可以讀【如何改變世界──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】,作者是美國的戴維.伯恩斯坦.這本書介紹了世界各地社會企業的例子,和背後推動的社會企業家,亦分析了這些機構和人物為甚麼能成功改變社會.譯者是【窮人的銀行家】的譯者吳士宏.吳士宏的故事也很傳奇,她是中國第一代打工女皇,曾任IBM, 微軟和 TCL 的高層.2003年,她高調離開企業生涯,立志要在中國推動社會企業.看她說做就做,首先就埋頭譯了兩本好書,似乎是來認真的,真的要改變世界.Labels: 讀書
 中學時,住沙田新田圍村,有一次在村口巴士站,看到一個巴藉小孩坐在凳上喊:「一蚊兩個咖哩角」,腳旁放了一大鍋咖哩角,看起來很好味.巴士站人流不多,原不是小販聚集之地.我想,小孩應是本村居民,母親不可拋頭露面,便叫小兒做小販幫補生計.記憶這東西真奇怪,二十多年了,今天我仍然記得他的聲音:「一蚊兩個咖哩角!一蚊兩個咖哩角!」
中學時,住沙田新田圍村,有一次在村口巴士站,看到一個巴藉小孩坐在凳上喊:「一蚊兩個咖哩角」,腳旁放了一大鍋咖哩角,看起來很好味.巴士站人流不多,原不是小販聚集之地.我想,小孩應是本村居民,母親不可拋頭露面,便叫小兒做小販幫補生計.記憶這東西真奇怪,二十多年了,今天我仍然記得他的聲音:「一蚊兩個咖哩角!一蚊兩個咖哩角!」Labels: 讀書

 很開心那天從旅遊書堆中挑了這本書<乾杯!柏林大街>,因為這不是一本旅遊書.作者簡銘甫是台灣人,在柏林生活遊歷了多年.他眼中的柏林,充滿了青春,反商業和無政府主義的氣氛,不是一般人眼中充滿藝術文化,歷史品味的歐洲城市,而是一個「正在誕生的烏托邦」.
很開心那天從旅遊書堆中挑了這本書<乾杯!柏林大街>,因為這不是一本旅遊書.作者簡銘甫是台灣人,在柏林生活遊歷了多年.他眼中的柏林,充滿了青春,反商業和無政府主義的氣氛,不是一般人眼中充滿藝術文化,歷史品味的歐洲城市,而是一個「正在誕生的烏托邦」.Labels: 讀書